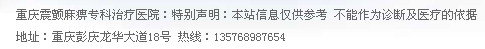董攀山我的白发亲娘散文
作者简介
董攀山
董攀山:山东定陶人。年12月入伍,年7月入党。历任战士,排长,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上校军衔。
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在《时代文学》《祝你幸福》《广西青年》《解放军报》《前卫报》《济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等文学类作品多篇。报告文学“一个英模的‘老三篇’”被收进原济南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英模事迹文集,在全区25篇文章中排在第三位,受到著名军旅作家李延国的好评。
著有长篇传记文学《我的军旅生涯》及《常用文写作探析》一书。
我的白发亲娘
(母亲-)
对我来说,年的春节是一个最悲怆的春节。这一年的大年初二,老母亲突患急性胰腺炎,医院紧抢救、慢抢救没能抢救过来,于两天后的初四晚七点四十分与世长辞,享年76岁。
母亲是在部队去世的。我当兵后,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除四姐家在陕西去一趟不容易外,大姐、二姐和三姐的家都在附近的邻村。按理说,她完全可以轮流到三个闺女家里去住,免得孤单。可是我们老家的习俗是老人一定要跟着儿子住,住闺女家似乎不那么好看。母亲要强了一辈子,自然不愿意叫人家说什么。想念我了,就到部队住几天。但是,部队有规定,亲属来队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间,加之母亲到我这里后,又总是挂念着四个姐姐和两个舅舅。于是,她总是在济南我这里、菏泽老家和陕西四姐那里碾转往返。
年,母亲已72岁,实在不能再在两省三地之间奔走了。这时,我已升任为原济南军区防化器材仓库政治处副主任。按照级别,仓库给我安排了一处宿舍。于是,我就把母亲接到部队,叫她跟着我生活。
随我生活的母亲共有两大愿望:一是天天能够看到我,二是每隔一段时间见孙子一次。我从机关到部队工作时,儿子已上三年级。考虑到儿子上学的方便,我没有搬家。爱人、儿子和岳母仍住军区司令部机关我原来的宿舍里,我和母亲则住在离市区较远的仓库宿舍。由于儿子在市里上学,祖孙二人不能天天见面,我就利用星期天该我值班的时间,把儿子接来和母亲团聚。看到孙子,母亲自始至终乐得合不拢嘴。她把姐姐们捎来的花生、红枣等好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一一让儿子吃。一边看着儿子吃东西,一边上下打量:看孙子又长高了没有,吃胖了没有,尽管中间只隔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看完外表还不满足,又把儿子的帽子摘下来,再看儿子的头。一边看,一边乐呵:“头来小(小是老家长辈对晚辈男子的昵称;对女子则称妮儿),我看看俺小得头。耶,扁头,哈……还很跟形势嘞。哈……”
在我们老家,庄稼人不讲究,小孩子生下来睡成什么头型就是什么头型,好多孩子都是后脑勺突出,成为“梆子头”。只有在我们村教书的小学老师的孩子,后脑勺才是扁平的。扁头可谓是身份和地位高的象征。母亲看孙子也是扁头,心里自然高兴。有时星期天该我值班时,儿子参加学校的活动来不了,母亲很是失落。“攀山,您小咋没来唉?”母亲问我。当我告诉她原委后,她又计算下一次我该哪一天值班。
可谓爱屋及乌。由于我是军人,老母亲对所有的军人及军人家属和部队职工都有感情。在家属院里,无论遇上谁,她都主动和人家打招呼,认识的称人家的职务,如“主任”“政委”、“处长”等,不认识的,如刚入伍的新兵,则叫人家“他大哥”(指我的大哥),表示对军人的尊重。有时哪位同志的家属、孩子来串门,她就像见到自己的子女、孙子和孙女一样亲,不仅拿出好东西给人家吃,走时还将孩子们的衣袋装满。仓库有60多个干部和志愿兵,春节前后家属集中来队时,哪个孩子是谁的,我分不清楚,可老母亲竟能一一对号入座:这个男孩是张助理员的儿子,那个女孩是王干事的闺女等等。一次,一位志愿兵的妻子来队生孩子,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满月时要到娘家住一住,说是这样做将来孩子有人疼。可她娘家远在老家,没法落实这一“规定”。母亲知道后,便把娘儿俩接到自己的屋里待了一天,说是孩子的姥娘不在,就叫我当一回孩子的姥娘吧!哈……唵,多好个小小,我就喜欢小小子!
年大年初二上午,我把母亲安顿好,回到市里的家里准备向有些亲友拜拜年。正要出门,仓库值班员打电话给我,说是老母亲肚子疼,还伴有呕吐,叫我赶快回去一下。我急忙赶到单位,看到母亲面色苍白,额头上还有点点汗珠,显然这是极度疼痛的表现。我带上司机,以最快的速度把她医院,经检查是急性胰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很重很重的疾病,上海市原市委书记柯庆施就是因这种病而去世的。治疗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手术,二是保守治疗。医生说,如果年轻,可以考虑手术,可像母亲这么大岁数,如果动手术,就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权衡利弊,最后决定保守治疗。
但是,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把所有能用的药物都用上,母亲的病情还是急剧恶化。她一滴水也不能喝,只是大口地喘气。到了下午,医生进一步会诊后告诉我说,看来老人家就是这两天的事了,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我不相信,昨天还有说有笑的,怎么今天说不行就不行了呢!但看到母亲那越来越急促的呼吸,我知道医生说的是真的。我叫妻子马上拍电报和打电话通知四姐和老家的人,医院里来。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见孙子来了,浑身插满输液管的母亲坚持着折起身来,“小,俺小来了小,来,给俺小钱。”边说边抖抖地从衣兜里掏出几张10元的票子,递到儿子的手里。那是我平时给她的三元、两元的零花钱,她一分也没舍得花,全攒起来并把小票换成大票,到年底作为给孙子的压岁钱。之后,她又非常吃力、断断续续地说道:“叫……孩子……好好上……学……要学好……当个好……人……要有……出息……”说完这些后,她只是大口地喘气,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初四晚,我和妻子正守在母亲的身边看点滴,突然母亲的呼吸弱了下来。我急忙到医生值班室喊医生。等我和医生一起赶来时,母亲已停止了呼吸。医生看了一下表:七点四十分。
许是极度难过的缘故,我没有哭,只是浑身不停地颤抖。娘啊,我的亲娘,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啊!您在床上躺上半年六个月,哪怕是十天八天的也好啊,让我好好地尽尽孝心,可是您没有。您说走就走,而且走在节假日里,唯恐影响我的学习和工作,一点儿也不愿意牵扯我的时间和精力,更不愿意叫我遭遇久病床前无孝子尴尬与无奈。您这是用自己一贯的风格,给儿女尤其是给我的最后的一次无私大爱啊!
父母一生共养了我们姐弟6人:5个姐姐和我这个唯一的男孩。在我两岁那年,父亲和刚满14岁的二姐因病相继去世和夭折,38岁的母亲领着我们姐弟5人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当时,我们家的生活来源有三:一是参加生产队的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分粮;二是种好分得的几分自留地;三是母亲的辛勤劳作。前两条都不是我们家的优势和长项,一伙孩子,最大的大姐才17岁,其他的一个比一个小,哪能拼得了体力、种得了地?一家6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母亲主要靠自己的两个手艺养家糊口,即炸面泡(一种圆形的油条)和编蒲扇(用蒲草编成的扇子)。把炸好的面泡和编成的蒲扇卖给街坊邻居或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一斤面泡赚3分钱,一把蒲扇赚5厘钱。利润低,便只好多炸、多编。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像一部不停歇的机器,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白天到集市上买蒲草,晚上借着月光编蒲扇。常常是我一觉醒来,都东方发白了,她还在“嗤啦”、“嗤啦”地编个不停,或和相对大一点的姐姐炸面泡刚刚停火,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赶到集市上去卖。正是靠着自己的辛苦劳动,母亲把我们姐弟5人一个个养大成人:4个姐姐先后出嫁;我也上学上到高中毕业,成为我们村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生之一,并且在整个上学期间从没有欠缴或缓缴过一次学费和书钱。无论平时还是过年过节,在吃上、穿上母亲都决不让我们姐弟5人次于其他多数人家的孩子。
母亲是一个刚强的人。
刚强的母亲唯一的一次求人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当时,地里的庄稼不是绝产就是产而不收,群众手里没有一粒粮,母亲连炸面泡、编蒲扇的本钱也没有了。4个姐姐饿得奄奄一息,我也脚、手、脸浮肿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看着快要饿死的我们,从不求人的母亲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拖着同样浮肿的身躯,第一次找了大队干部和下村了解情况的公社领导。第二天我家便分得了几块棉饼和一篮子醋糟等在当时堪称救命的食物。
“不能忘了公家!”母亲时常这样告诫我们。
闺女多、儿子少,这就决定了从旧社会过来的、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母亲愈加重男轻女。在我们姐弟5人中,她总是毫不掩饰地向着我,偏4个姐姐。用邻居的话说,在我们家,吃先急着我吃,喝先急着我喝;有时同样惹母亲生气,对于几个姐姐母亲是真打,而于我则是将巴掌贴在我身上轻轻地推。正是这由衷的疼爱,也使母亲在重大问题上决不姑息和迁就。
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段时间一度产生了厌学情绪。这天早饭后,我邀了两个要好的同学以给羊割草为名,到村前的河沿上玩了一上午,没去上学。中午回来吃饭时,母亲手攒一把柳树条儿堵在了门口。
“做啥去了?”母亲脸色铁青。
“割草去了!”回答得还很理直气壮。因为经验告诉我,那把柳条儿不过是演戏用的道具,母亲不肯对我怎么样。
“唰!”柳条儿刮风般地抽来,我的胳膊上、脊背上即刻是道道血痕,疼痛钻心。
从小就娇生惯养的我,哪受到过如此的委屈!不但不狼狈逃窜,还挑衅性地往前凑。
“唰!唰!唰!”柳条儿雨点般的落下,丝毫没有手软的意思。在场的三姐、四姐看事不妙,一边用身体挡住飞舞的柳条儿,一边拿出刚出锅的两个窝窝头哄我朝学校走去。当我刚刚走到院门口,就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我知道,那是打在我身上,疼在她心里!
这顿皮肉教育效果很好。从此,我的学习成绩一路领先,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始终保持在前三名,并且一直担任班干部。每当我把三好学生的奖状捧到家里时,母亲总是笑呵呵地从攒钱买盐的鸡蛋篓里,挑一个最鲜最大的鸡蛋煮上,然后亲眼看着我吃下。
客观上讲,母亲是一个弱者。但他从不示弱,总是以强者的面目同情和关心每一个人。有要饭的要上门来,无论多少是一定要给人家点东西吃的,决不允许我等出言不逊,把人家赶走;遇上夫妻、兄弟、邻里之间有吵嘴打架什么的,她拼命也要把双方拉开,有时狠不得同强势的一方对打起来,尽管哪一方都比她有劲;我们姐弟很小的时候,她总是无偿给邻居家无奶或少奶吃的孩子喂奶,待姐姐们生儿育女时,她仍要求姐姐们这样做。隔壁的堂嫂提醒她:
“闺女听你的,就不怕女婿有意见,饿坏了外甥、外甥女怎么办?”
“那我就连女婿一块儿卷(骂的意思)!”母亲说。
这里,很有必要提及一下小大娘。
小大娘是我远门的一个地主大爷的小老婆。这并非我的那个地主大爷多么风流奢侈,是因为第一个老婆不生育,便又找了个小的延续香火。正是因为是小婆,家庭和社会地位低下,小大娘的一生很是凄惨。年轻时不但受公公、婆婆、丈夫的打骂,还常受大婆的欺负,比别的劳动妇女还多了一重压迫。年老又患了神经病,不犯病时跟正常人一样,一犯病就手舞足蹈,嘴里唱着自编的对现实不满、对领袖不敬的顺口溜。这在“文革”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为此,她经常遭批斗。每次批斗完,家她是不敢回的,因为上面要求她们家要搞好“家庭批斗会”,继续对她进行批斗,否则将拿她的子女说事;怕受连累,其他邻居也不敢接纳她;唯一敢于接纳她的,就是我母亲。看小大娘来了,母亲先是给她盛上饭,让她和我们一块儿吃;然后又陪她说宽心的话儿,要她往好处想,千万不能寻短见。天晚了,还安排她住在我家里,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正在上初中、还想加入红卫兵的我坚持不住了。一次,我对母亲说:
“娘,别让小大娘到咱家来了中不?同学们说我立场不坚定哩!”
“你知道啥,”母亲勃然大怒,“一个苦老婆子,能看着人家去死!”
品尝过柳条抽打是啥滋味的我,不敢吱声了。
(作者、母亲、儿子。摄于年夏)。
后来,小大娘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对此,母亲很是不以为然。她不止一次公开或半公开地说小大娘冤枉,不该法办。并说,小大娘才是真正的穷人嘞,大户人家的闺女谁肯给人家做小老婆呢,只有穷得没法儿了才走这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大娘得以平反,历史证明了大字不识的母亲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我想,这并非母亲有什么先见之明和多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她甚至连精神病人在犯病期间犯法不负法律责任这一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只能证明一点,就是她的正直、善良与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从根本上说来是一致的。她对人的爱,是不分尊卑、贵贱、穷富、强弱,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甚至敢于承担风险、舍己为人的真爱;是超越阶级、阶层、亲疏、远近,面向所有人的大爱;是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又符合现代社会要求并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永恒之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母亲也分得了一定量的责任田。这时的母亲已完全没有能力种地了,只好由别人代种,然后象征性地给点收获。就当时的情况看,还没有在生产队吃“大锅饭”时来得现成。可母亲没有半句怨言,她总是乐呵呵地说:
“家家都有啥吃了多好唉!”
这就是母亲。她决不以自己的得失论是非,她首先白癜风方法白癜风能吃什么药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qmqc.com/zcmbzz/8563.html
- 上一篇文章: 轻松一刻奇葩患者20例总有一款气哭你
- 下一篇文章: 来慢茶馆吃货妄图吃垮自助餐餐厅撑